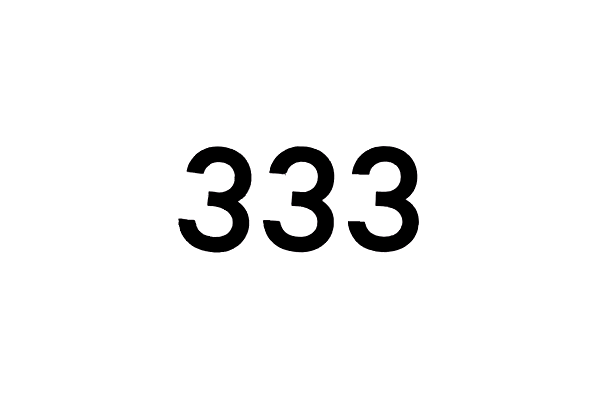王懿泉,以小泉的名号行走江湖多年,拥有多重身份:策展人、艺术家、事务所合伙人、艺术媒体人,而这些身份的触发地均是他的工作室。
小泉的工作时间很规律,朝十晚六。在工作室,他有50%是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和WHYNOTTHINK咨询的合伙人,20%是一位艺术家,25%是一位策展人。至于剩下的5%,他说自己是一个吉祥物。
Q:你认为这些身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A: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手不同,你要知道你在与谁上演对手戏。比如说,作为艺术家,你要与文化(这个庞大的知识领域)以及艺术史(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一起拍戏,还要演好你的艺术家角色。
对于多重身份所使用的工作空间,小泉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关键词是“可持续”,指一个让人有动力来的环境,舒适自洽,安静不被打扰。“不可持续的工作环境,是虚假的,你干不下去的。”
办公桌是可持续工作环境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小泉的办公必需品如下:
当我们问起小泉实际生活中是否需要艺术品时,他很笃定地回答:“需要”。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买一张电影票或一张CD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收藏。
“收藏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文化行动,其实乐趣蛮多的。而我的收藏不算多,我还在慢慢培养收纳、保管、珍藏、爱护、传递的文化艺术品的能力。”
小泉的收藏围绕着当代视觉艺术作品展开。如果喜欢一件作品,他会先去调研这位艺术家早期的作品,他认为那些作品往往更具有时代意义。小泉也重点关注同辈艺术家的作品,在买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的同时,也给予了艺术家们支持。
摄影:申佩玉
Q:由你策展的展览「吾辈」正在展出,和我们介绍一下吧。
A:这是一场献给今天和明天的展览,也是献给所有参展艺术家自己的展览。我特别高兴能和33位参展艺术家一起完成「吾辈」展览。
展览和空间可以按顺时针概括为:一个关于纽约的小角落、一面全是艺术家形象的长墙、一面关于特定时间和运势的短墙、一个虚构的便利店、一些工整的对仗、一间放映厅。
Q:「吾辈」以代际为出发点,聚焦与你同辈的艺术家们的创作实践与艺术思考方式。代际关系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自己的生活或工作方式?
A:我是由20后带大的孩子,你猜代际是如何影响我的?
从前我在祖父祖母的口中总听到“老一套”这个词,我上大学后觉得这可能就是old-school吧。我是一个喜欢老派的人,我也喜欢老派的人与事,比如,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文武双全的普通人,儒商,耕读世家和书香门第,八九十年代白手起家的奋斗者(《大江大河》里的小杨)。
我还很喜欢和比我年长的人交朋友。
Q:聊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A:今年十一月下旬,我会在厦门的第八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策划两场个展,参与摄影季的主竞赛单元“发现奖”的角逐。我很荣幸能担任这个项目的策展人。
除了当代艺术,我还有一部表演艺术、当代舞蹈项目正在进行全国巡演。九月上旬,我长期合作的香港舞蹈家杨浩在广州大剧院和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办了舞蹈剧场作品《浩浩传奇》的两站重要巡演。我是这部作品的制作人。冬季,我和杨浩还会继续巡演到不同城市,为困难的2022年画上一个完美巡演的句号。
小泉在疫情期间参加了3ge3厨王争霸加时赛,来回顾一下他的精彩表现:
《孤独的两个》
两块⻩,
六块红,
一黑一白,
十二块绿。
两个人,
二十六天。
吴佳音,
王懿泉。
—小泉
Q:解封后还在做饭吗?有没有研发新的拿手菜?
A:最近也在做饭,习惯了在家里做饭吃的感觉,当然,没有封控时候的必做每一餐的规范。因为这太难了。最近做了几次手抓羊肉,其实很简单,羊肉放进凉水静置、配料(洋葱、胡萝卜、肉蔻、花椒)、高压锅。做这道菜我还在研究如何做得有祖先的古法,一个心得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Q:除了做饭,封控时还有哪些活动占据了你比较多的时间?
A:看电影。找各种片子来看,有教无类,照单全收。还有就是封控期间我在准备参加香港CHAT美术馆的展览,我的一个表演作品是在5月演出,所以我有很多时间是和我的合作舞蹈家杨浩一起线上创作舞蹈作品。
Q:最近在看什么书,推荐一下吧。
A:上周我在富阳刚买了一本《鱼翅与花椒》,正在读。是英国作家和美食家扶霞(Fuchsia Dunlop)的书,关于中国饮食文化和她对川菜的研究,非常社会学,非常散文化。
案头,解封以来在我笔记本电脑底下的是俄罗斯汉学家张霞(Katya Knyazeva)《Shanghai Old Town: The Walled City》。
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书是,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 (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和中国作家和画廊家胡昉的《新人间词话》。